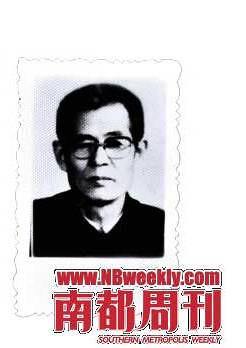南都继续V5!庆幸吧,我们的时代。继续努力吧,移民美利坚
一个酷爱篮球的高二少年,陈宗海,因为一个不高明的玩笑,从此被划为“右派”送往夹边沟,此后又以反革命团伙罪名送监。十年农村改造,摘帽后草草退休,荒诞一生。
陈宗海,1979年平反时拍摄的照片。陈宗海一直保存着他的平反文件。
2010年10月,陈宗海,家中。
当孙子还是赖在陈宗海怀里使劲撒娇的年纪,他仰起脑袋,向瘦高的老头发问:爷爷,你年轻时干啥呢?—我呀,我在意大利踢足球啊。爷爷你说个意大利语呗—拉密密塞脚沟,这是发界外球。
他是胡诌的。如今孙儿业已成年,那个俏皮的谎言仍时常被拿出来,供大家哈哈一乐。80岁的陈宗海像所有城市老人一样享受着耄耋之年的乐趣,高兴时就出来公园里观光,不高兴就睡大觉看电视。他爱看《百家讲坛》和NBA,尤其是后者。42英寸的液晶屏幕里,大洋彼岸激荡的惊心肉搏,老爷子看得如痴如醉。
与儿孙们聊天,多是家常细琐,陈宗海努力扮演好家庭中长者的角色。他记得当年父亲的治家之道:小事不唠叨,大事平心静气讲。那么,自己的过往算什么呢?算不上大事。晚辈们不问,他也懒得提。大家只是隐约知道,老爷子年轻时当过“右派”,送到夹边沟,吃过苦头。
他很少出门。如今保持走动的还都是初中时代的朋友,人家来叫,他便配合着过去。坐在他们中间,他觉得自己永远是一个陪聊。对于社交,他提不起一点点兴趣来。
去年冬天,陈宗海找一个中医大夫看胃病。大夫说,你这么大年纪,性情还这么暴躁,是生气造成内消化不好。陈宗海抱怨:我是抑郁症,过去的事情老忘不掉。现在还梦到夹边沟,好像有人找我,心跳得突突的把自己惊醒。
他尽力避开生活里的一切毛像,那是他荒诞一生的根源。
“我相信人是有命运的,”陈宗海说,“我不偷不盗,怎么能有牢狱之灾呢。怪,哎呀,我的妈,真可笑。”他摇摇头,两眼放空,不住自嘲。他埋怨自己年轻时手欠,信手在报纸上涂上的那几笔,毁了一辈子。
眼泪
那些生命中最绚烂的年华,已如祁连山的雪水般悄然流走。六十年前,中学生陈宗海看着共产党的军队开进了兰州城。对于新政权,他毫无概念。
陈家是一个手工作坊家庭。大清朝的曾祖父传下来的300亩黄河盐碱地,却在百年后土改中为老陈家戴上了“半地主式富农”的帽子。祖传做砂锅的手艺让陈宗海感到厌倦,他认为太没技术含量。他成了兄弟姐妹中唯一上学的。
1950年,20岁的陈宗海考上西北师大附中。他酷爱篮球,爱打最出风头的前锋。如今他做到的好梦,多半是自己在篮球场上奔跑的身影。
对于未来,他并无打算。在可供挥霍的青春里,学而优则仕一类的梦想被远远抛在天边。朝鲜半岛的战火烧到边疆,中国决定出兵。陈宗海亦无太多触动。他承认自己并无太多政治觉悟,他只愿无忧无虑地打球。
或许,以后去当个运动员吧,他想。但很快,他还是被裹挟进强大的政治机器。
毛岸英战死的消息从远方传来,校园里人们窃窃私语,小心猜测着中南海的反应。有天,他像往常一样往课桌上铺了张报纸。报上有张毛泽东的照片。他盯着他看,他为他感到难过,老年丧子的哀痛仿佛一样笼罩着他。他拿出钢笔,给画中人添上了几滴眼泪。
他被指为思想反动,污蔑伟大领袖。校方要求他写材料,交代自己的思想。他生平头一回感到政治的压力,他害怕极了。在检讨中他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对毛主席的污辱。批判会上,积极分子振臂高呼:打倒陈宗海的反动思想!
他暗自庆幸,毕竟不是打倒陈宗海。阶级斗争在此时尚没有多年后那般狂热和偏执。但没完没了的汇报检讨,却让陈宗海觉得丢人现眼。读完高二,他决定退学。
劳教
那个时代的工作没有几十年后这般难找。陈宗海想得简单:找个工作换个环境,就没事了。在家帮父亲做了半年砂锅,他认定自己太过大材小用。表叔介绍他去兰州市建筑公司,当伙食管理员。买菜算账,管工人的吃喝拉撒睡。虽然是干部身份,但他心里却不情愿。
1954年元月,建筑公司搞冬训。内部肃反开始了,所有人都要交代1949年前的底细。陈宗海认为与己无关,便不发言。领导开会时发话:有些人犯过严重错误,还不主动交代。陈宗海一想:这不冲着我来的吗?但谁能证明他的清白呢?这样下去岂不又是没完没了。他觉得自己搞定不了这事。左思右想,他向单位请了个长假,回家了。
1955年年底,兰州开始公私合营。陈家的砂锅作坊和其他几家砂锅作坊合在一起,组成陶器手工业合作社。此时的陈宗海已经结婚生子。公私合营前,全家凭靠父亲一人的手艺倒也过得去。但合营后所有人都变成了工人,他不能再赖在家里啃老。合作社领导说:你都这么大了,还指着你爹过啊?他当上了合作社的会计,每月工资六十元。
进入1956年,形势加速变幻。陈宗海的会计没当上两个月,就被七里河区轻工业联社成立的职工业余学校调去当扫盲教师了。白天给领导些材料搞宣传,晚上给学员上课。
“大鸣大放”里,陈宗海一句话也没敢说。领导找他:你谈谈嘛,总有些看法嘛。陈宗海心想,给毛主席画眼泪的事让他晦气了好几年,我哪还敢说什么。
一天开会,陈宗海和另一个老师一起抽烟。一片乱哄哄中,整风小组组长宣布:现在开始开会。陈宗海,你不要再说话了。陈宗海大为不忿:我只是抽烟,没有说话啊,你怎么胡点名呢!
第二天,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席卷而来。给毛主席画眼泪的旧事被抖出来,衍生的各种批判如乱箭般飞向陈宗海,他奋力争辩。1958年4月10日,整风小组领导宣布,陈宗海问题严重,态度恶劣,定为“右派”,保留公职,劳动教养,送往夹边沟。
他记得在领导宣布的劳动教养条例里,曾提到不愿参加劳教的可以开除公职自谋生计。他打算放弃公职,这样就能免于劳教。但学校有个反右积极分子来到陈家,向陈母借走了家里的户口本。陈宗海晚上回家一看,自己的户口已经被注销,下面写了一行字:迁往夹边沟农场。“这个王八蛋叫安殿策。”提及此事陈宗海仍难掩愤怒,“人和人的关系已经划到阶级敌人了,再没啥客气了。”
家里老父亲说了一句:“这一次不得了。”陈宗海却不以为然:最多一两年。他亲眼所见,1949年的肃毒运动中,旧社会的抽大烟的人被关进戒毒所劳教,国家管饭,一两个月到半年,有些轻微劳动,戒了毒就给放回来。“我还没坏到吸毒那程度,时间还能长吗?”
求被捕
在夹边沟,陈宗海认识了俞兆远。
俞兆远是兰州市西固区劳资科科长,因为一句“征公粮再卖给农民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”被打为“右派”,送到夹边沟。这是个聪明人,在夹边沟口粮再吃紧的时候也没有找家里要过一分钱。俞兆远跟管教干部和分队长混得好,“劳动偷懒耍滑不出力,到处偷吃的”。在这里,他与陈宗海成了好哥们。
陈宗海积极改造的愿望终于在1959年的劳动节彻底破灭。三千“右派”在此前的劳动中拼尽全力,却只有三人被宣布摘帽。回家的希望的越来越渺茫,这年国庆过完,陈宗海一下子垮下来,连打饭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俞兆远看陈宗海累成这样,便跟队长建议,把陈调去放水组。那是个轻巧活,挖口子堵口子。重要的是,休息时可以在菜地里偷庄稼吃。
“偷着吃,不偷活不了,”陈宗海说,“可能我比别人偷得还多一些。”陈宗海偷大田里的东西,土豆、洋芋、糜子、麦粒,一切能吃的都偷着吃。但他有个原则:偷公家不偷私人的,别人的东西不能偷,那都是救命的。
有天夜里,陈宗海跟俞兆远闲聊。俞兆远无意中说起,老家有人过来探亲,说城郊农场劳改犯的生活比这里“右派”好得多。劳改犯每天只劳动八小时,每人每月的口粮是四十斤,这比那却是十个小时以上的工作量,口粮却只有二十四斤。那边饿死犯人的事比夹边沟少得多。
陈宗海怦然心动。他寻思能不能自己也换个身份—变成犯人去城郊农场。
五月的一个夜晚,他打死了一头猪,跟人偷偷分了吃了。他的计划是,来一次刑事犯罪,够判刑,一两年就成。但此事竟无人发觉,陈宗海又喜又忧。喜的是吃到猪肉,忧的是获罪计划没能成功。他又偷了一只羊,还是没人来找他。
“反革命”
1960年9月,夹边沟“右派”转移到明水。国庆节时,农场来了个小个子年轻警察,他对陈宗海说,你们怎么还休息呢,要好好干啊。陈宗海隐隐觉得此人有些蹊跷,他玩笑回应道:哎呀,我都把帽子给忘了。
过了几天,警察把陈宗海叫到办公室,向他宣布:兰州市城关区法院以反革命罪逮捕陈宗海。
大组长已经把陈宗海的行李拿来,警察给陈戴上手铐。第二天陈被送上火车,押回兰州。在看守所关了几个月后,陈宗海被宣布五年劳改。
这下算是了了陈宗海一桩心愿,此时每天周围都有几十人在饥寒交迫中死去,他终于可以不在明水农场等死了。但自己怎么就“反革命”了呢?
来夹边沟前,陈宗海与夜校的两个同事合了张影。照片背后写了一行字:让我们的友情如森林长青。任凭它惊涛骇浪,也阻止不了我们对真理的信念。陈宗海把照片挂在家里,过了几天领导找他谈话,说有人举报,照片后面是他们的反革命誓言,三人里通外国,准备发展组织逃到印度加尔各答去。陈宗海大怒:哪个王八蛋造的谣,想把我往监狱送么?
两年后陈宗海果然因此事被送进了监狱。进夹边沟后,他的所有通信都在公安监控中。公安调查得出的结论是,陈宗海等三人是反革命组织,判决陈宗海五年有期徒刑,那两位同事分别被判四年和八年。
在一种惊喜交错的荒诞感中,陈宗海开始了纳鞋底的劳改生涯。犯人自然不如“右派”们处得舒服,但监狱里10年也死不了,夹边沟再蹲1个礼拜也许就挂掉了,陈宗海想,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。一年零两个月后,合议庭推翻了之前的“反革命”判决,他被宣布无罪释放。
陈宗海回到家里。老母亲看着儿子心疼得直摇头,眼泪巴拉巴拉掉,一句话说不出来。
对于“右派”来说,并非所有人回到家里都能迎来笑脸。两年时间妻离子散物是人非者大有人在。俞兆远回到家中,妻子向他提出离婚。理由是,俞兆远在夹边沟吃惯了偷来的生粮食,回家两年,还要偷面柜里的苞谷面吃。邻居们都说,俞兆远的女人不让他吃饱,逼得丈夫偷家里粮食。
下乡
麻烦很快又找上了陈宗海。居委会让陈去派出所参加“学习政治”,月月写思想汇报。从1962年搞到1969年年底,政治学习一直没有间断过。
陈宗海买了一辆架子车,加入街道组织的车队拉货度日。拉车第一天,陈宗海心里百味杂陈,自己曾经也是个干部啊。又安慰自己:我不是骗人,凭劳动吃饭嘛。一个月下来他能拉到158块,扣掉税款,剩了104块。
好景不长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,架子车的工作也保不住了。1969年,陈宗海作为黑五类分子被遣往农村劳动。孩子老婆还有那辆架子车,一块交给了70 岁的父亲大人。他的下一站皋兰县青白石公社,是陈家的原籍。距离兰州城100华里(1华里=500米),步行一天就能到。
大队里只有他一个“右派”,周围都是农民。大家都知道他给毛主席画了眼泪,倒也没人因为“右派”欺负他。农业社会的古朴和务实,部分消解了政治高压的恐惧。陈宗海与所有人一样下地干农活,一起吃大锅里的稀饭,他与所有村民知根知底。在经历了短暂的陌生后,村民们会毫不犹豫地接过陈宗海递过来的烟,一起吞云吐雾,上天入地胡侃。
陈宗海却暗暗为他们悲哀。“我现在就想啊,人确实好骗。在农村里蹲了10年,上面说他们是贫下中农,工人农民是领导阶级,他们就高兴得整天在那里刨地。”
反倒是几月一次的探亲,却慢慢从兴奋变成了沮丧。穿过一路枯燥的风景,陈宗海蹬车回到兰州家里,同学和亲戚已中止了与陈家的来往,邻居们闪烁微妙的眼神让他惶惑。他更愿意蹲在农村,在那里,没人在乎他是一个“右派”。
上世纪80年代时,他看到谢晋的电影《牧马人》,不禁哑然失笑。电影主人公许灵均也被打成“右派”,来到西北牧场劳动。老牧民视他如至亲,一个漂亮的姑娘还看上他,俩人有了一片无忧无虑的小世界。“我们哪有那样的好运气!”陈宗海感慨,“农民只是占小便宜,所以忘记了阶级斗争。”
这次陈宗海不再敢预计归期。每年大队开大会,让群众评议陈宗海一年的表现。“他没干什么坏事,干没干好事不知道。”大家每年都这么说。每年评审报上去,结果却总是如泥牛入海。到最后,陈宗海不禁怀疑还有没有回城的可能。他一遍遍自问:“右派”帽子真的是终生的么?
毛泽东逝世时,陈宗海跟家里找招呼:啥也别说。大队开追悼大会,不让陈宗海参加,“其实我也不想参加,”陈宗海说,“我觉得没了他事情会好一些。”他曾被挂上牌子,向毛主席相请罪。但他觉得这算不得什么,“‘文革’于我有利,毛这个事毁了他自己。”
平反
1978年12月的一天,俞兆远走在兰州街头。路边电线杆上的大喇叭里开始播出那次著名会议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。俞兆远漫不经心听着,他觉着越听越入耳,最后他趴在栏杆上,竖起耳朵听完了全文。公报中有一段话,讲到了平反问题:
会议指出,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、有错必纠的原则。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,纠正错案,昭雪冤案,才能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,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。
俞兆远想:这下有出头的日子了。
实际在半年前的4月5日,《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》已获中共中央批准,摘帽工作以及“右派”的安置问题在之后的几年里陆续完成。
1980年10月,陈宗海盖完最后一个章,他拿着画满各种迁入迁出标记的户口本回到家里。从此他再不是一个“右派”。他拿到一千块钱的赔偿,这大约相当于当时工人一年的工资。钱拿到手,他总觉着是一笔意外之财。
俞兆远也拿到6000元赔偿。周围人都说,老俞发财了。俞兆远说,“我穷的时候谁都不上我门,现在什么事都来找我,借钱?算了吧。谁都不借。”
很多人没有拿到任何赔偿,这是个伤脑筋的问题。另一位“右派”刘光祖在退休后的十余年里,坚持为自己在平反前被扣除的工资奔走多年,他找单位、市委、省委……写过无数次申诉,无人能为此事负责,或者给出解释。2007年,老人在病中郁郁而终。
父亲劝陈宗海,如果对赔偿定案不满意,可以写申诉材料。陈宗海摇摇头:我没有啥意见,有补偿就不错了。弄不好再加个处分怎么办?近几年,关于“右派”索赔的呼声开始多起来,陈宗海微笑摇头:我没想过要赔偿,没戏的。
陈宗海再次回到家中已经四十九岁。此时距离他戴上“右派”帽子,20年弹指一挥间过去了。熟人说:老陈你现在怎么这么不修边幅了呢,五十年代还挺时髦啊。是的,那会儿还能花半月工资去买双漂亮的小方头皮鞋。在农场、监狱、农村,哪里还有讲究的条件?现在呢,老了,没心情了。女儿给他买衣服,他不愿要。他觉得对家里亏欠太多。
像是完成了某种交接,在陈宗海摘帽半年后,85岁的父亲撒手西归。在之前的20年里,父亲一直在打着零工帮陈照顾妻儿,这个家庭终究得以保全。在陈宗海遥遥无期的等待时光中,他的头脑中一直告诉自己:要活下去,一定不能在父亲过世前死掉,那就是不孝。
在文教局又干了九年小学教员,陈宗海退休了。如他之前做过的所有生计一样,人生的最后一份工作也没能给他带来任何成就感。“没有那个事,我可能就是个运动员。”他喃喃道,眼中掠过一丝遗憾。
2008年,陈宗海在一张报纸上看到章诒和《往事并不如烟》的广告:旧德的精彩。他并不知道这也是一本讲“右派”的书,但出于对“旧德”的兴趣,便上街买了一本。同是“右派”,他却感到强烈的隔膜。书中主角们是他在学生时代耳熟能详的“大右派”,他们在运动后依旧开着小车,住着大宅。他开始为半世纪前的那场运动感到困惑:“‘右派’与‘右派’简直相隔十万八千里,反右—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?”
几乎所有的接受采访的“右派”,都会特别说明一句:平时,我很少提起这些事的,这些经历总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来。人年纪一大,近期的事情忘得快,那些遥远的记忆反而清晰起来。俞兆远怕说夹边沟, “一提这个事,就好几天都睡不着觉。”他每晚睡觉前要喝上三杯白酒,带着几分醉意,沉沉睡去。
2008年,俞兆远跟家人来北京旅游,他终于见到了毛主席。在万千热切的瞻仰者队伍里,俞淡淡地看着那位静卧的老者,在心里说:你这个老人家,过去制定的政策,不但对我不利,对好多知识分子也不利啊。
杖朝之年的俞兆远拒绝给自己做寿。摘掉“右派”的帽子后,他越发觉得人生虚无。有个熟人60岁做寿,过后不久便撒手人寰。他感慨寿宴上那些红花绿花,瞬间就变成了灵堂里的白花。
当年是谁揭发了陈宗海?陈说他知道那人,是同班同学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,俩人各自带着妻子,在兰州街头面对面撞见了。彼此微微点了下头,便擦身而过。走出去几步,陈拉拉老婆,“这就是当年揭发我的人。”他回过头,那人也与女人回头看他们,像是说,看,那就是给毛主席画眼泪的家伙。
恨他么?不恨,陈宗海说,我一点都不怨他。从此他们再未碰面。